在前两篇文章中,我曾说《巨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小资产阶级的反战,有读者指出巨人在看海篇以前并不是反战的,这位读者是非常敏锐的。《巨人》的主题事实上是有两个,前一个主题是“自由”,后一个主题是“战斗”。两个主题以看海篇为界限,而看海篇前后的故事在风格和视角上的变化,也是这种主题变化的最直观的表现。同时,通过观察谏山创对两个主题思考的深度变化,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那就是马莱篇以后的故事原本并不在谏山创最开始的故事大纲里,很有可能是谏山创在内外因素的驱使下临时加入的篇章。
谏山创非常擅于在不同的剧情中采取相同的分镜与台词来执行某种对比,为后面的剧情赋予额外的讽刺意味。就艺术效果而言,这种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但这种手法也会掩盖一些概念上的不同。换句话说,有些时候这种所谓的对比在逻辑层面是根本不成立的,作者只是用相同的分镜和台词让读者产生错觉而已。
在《巨人》的两大主题上,这种错觉尤为明显。
看海篇前的“自由”是相对于墙的概念,人类出不了墙,所以是家畜,所以不自由。(虽然肯尼的遗言对自由有更深的探讨,但由于只被利威尔听到,实际上对主线剧情没有产生影响)
看海篇后的“自由”是更为抽象的概念,阿明的不自由是他人的记忆影响自我意识后对“我是否还是我”的怀疑,艾伦的不自由是当前行为受未来记忆影响而产生的时空悖论,二者实际上是对物质与意识孰为第一的哲学问题的探讨。
看海篇前的“战斗”是艾伦对三笠的劝告,要战胜的是自身面对强大敌人时的恐惧情绪。
看海篇后的“战斗”是艾伦对自己和耶格尔派的劝告,要战胜的是杀死同类的罪恶感。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看海篇前后的“自由”与“战斗”所讨论的根本不是一个范围的内容。看海篇前的自由与战斗都是很纯粹的概念,是为剧情服务的存在。而看海篇后的自由与战斗是对更高深的哲学、伦理学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是剧情要解答的问题。
简单归纳一下的话,《巨人》的整体结构是这样的:
看海篇之前,自由与战斗都是确定的概念,其中自由是要战胜巨人,战斗是要战胜恐惧。两个概念里,自由是始终贯穿剧情的主线,战斗主要集中在前中期对巨人不了解的情况下,推动主角团战胜恐惧参与战争的剧情中。
看海篇之后,自由与战斗都变成了不确定的、需要解答的问题,其中自由是对物质与意识孰为第一的询问,战斗是对战争中是否应遵循道德的询问。两个问题里,自由游离于剧情之外,可解可不解,战斗是始终贯穿剧情的主线,并且必须给出解答。
也正因为看海篇前后关于“自由”与“战斗”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的变化,导致前后剧情在内部逻辑上的割裂。但谏山创却试图通过对剧情与台词的包装来营造一种前后剧情连贯的假象,在“自由”已经不是剧情主线的情况下依然强行往剧情里添加相关内容,最后产生诸如麻将桌上的自由、云上的自由以及格里沙抱孩子的自由这类匪夷所思的剧情。
而谏山创花了大篇幅去讨论的这两个问题,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结论。对“自由”的讨论流于表面,实际根本没有给出解答。对“战斗”的讨论陷入虚无主义,最后给出一个“只要不杀光就是有道德”的反人类结论。
关于“战斗”的问题,在前两篇文章已有探讨,本文不再做赘述。
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待自由,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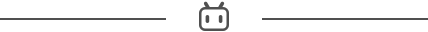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自由包含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是哲学层面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称为“主观能动性”;一个是政治层面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称为“自由”。
鉴于谏山创所讨论的是哲学层面的自由,所以我们首先从主观能动性说起。主观能动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相比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论与唯心主义的唯意识论,主观能动性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即:
物质决定意识,先有物质后有意识。
意识不是单纯被动的认识物质,而是可以有选择地、主动地去认识物质。
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先有意识后有基于意识的物质,但在意识之前一定有另一个物质作为意识的来源。
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是有局限性的,规律客观性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论述,我们可以对《巨人》后期的“自由”问题进行解答。由于物质决定意识,一个人获得了不属于他的记忆,本质上是他获得了一份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他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实际属于对于认识的再认识,和看了一本书是没有区别。试问,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因此自身对于物质的认识有了改变,他是不自由的吗?刚好相反,他的意识有了变化正是说明他拥有主观能动性,正是说明他能主动地、有选择地认识物质,正是证明了他的自由。
只要不将意识神圣化,而把意识单纯看作客观物质在主观世界的反映,很多唯心主义哲学上的难题实际根本不难解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制约人在哲学上自由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教员说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天下的事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因为客观规律导致人接触不到某个物质,所以人有认识上的不自由。
因为客观规律导致人的实践无法达到预计的效果,所以人有实践上的不自由。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不自由,莫过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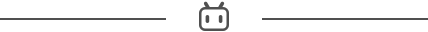
关于政治层面的不自由的理论,主要来自恩格斯与列宁对于资产阶级普选政治的批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的眼光看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务,而从阶级的角度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压迫的暴力机关,因此“自由的国家”这种说法属于纯粹的诡辩,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剥削阶级都没有参与政治的自由。注意,这里不是说被剥削阶级的所有个体都不能参与到政治中,而是从整个阶级的层面看,被剥削阶级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完全不能和剥削阶级相提并论。资产阶级普选政治的虚伪之处正是如此,他们一方面高呼自由、歌颂民主,另一方面却在人民参与政治的道路上设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准入门槛,这些门槛单拿出来似乎并不能阻碍人民参与到政治中,但所有门槛加在一起便使得人民在事实上被隔绝到国家政治之外。
恩格斯与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从来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因此国家最终是要被消灭的,但消灭之后要以另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公社”)替代其在社会生产上的管理与协调的职能。而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只有在公社中才能真正实现。
而在公社建立之前,所有国家之间的矛盾本质上都是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而非被剥削阶级的矛盾。马莱与帕岛看上去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下,实际上是马莱剥削阶级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长期为马莱人民灌输种族歧视理念的结果,而并不是马莱人民与艾尔迪亚人民真的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对于艾伦在地鸣篇所犯的两大错误便能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没有认识到马莱人民并没有政治方面的自由,把“反艾”当成是马莱人民的共识,违背了统一战线的原则。
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实际上的领袖,不能仅凭个人意愿发动战争,而要与广大同胞,尤其是与广大被剥削阶级进行商议后,在达成意志上的统一后再组织发起战争。这与军队的物质存在形式无关,而是一个进步的领袖应有的政治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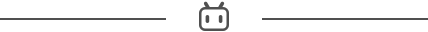
谏山创自身对于政治与哲学的一知半解,加上强行更改原本的大纲结构引入新的过于严肃的内容,共同造就了《巨人》这部作品灾难性的结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谏山创对于故事中的各种问题有过积极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巨人》前中期许许多多思想上的闪光点,但在最核心的关于自由与战斗的问题上,他却给出了最反动的答案。
教员曾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谓越思考越反动,谏山创便是最好的例证。
